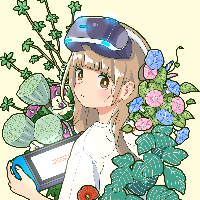竹林
端午刚过,冷不丁来了一场降温,让月月家孵的一窝鸭蛋全都夭折了,闽家爷爷把蛋壳和初具雏形的一些东西装到破麻布袋里,让月月送到河边那窝牛竹上挂上。
如果见过牛竹,这是一种我们当地特有的竹子,直径能到三十多厘米,可以长十七八米高,材质坚固,三年开花,枝丫有刺,沿着主干两边上下错开、左右对称的长着和牛角一样的弯角,像是一个天然的楼梯,可以一直沿着角爬到高处去。
将夭折的蛋壳挂在竹枝上,是一种俗成的处理方法,操作并不复杂,用一根竹竿把那个口袋挑起来,然后挂到竹枝上,下面点几根香即可。我们没有追究明白这里头有什么门道,不过村里习俗众多,也是顾不过来。
月月找了根竹竿,挑起那个很臭的袋子走了出去,我也从院墙上跳下来,接过闽爷爷手里的打火机和香跟上她。
那窝牛竹就在她家对面,远远的踮起脚便能看到。此时院墙外黄昏将至,太阳挂在山头上,把山的影子拉得老长,盖住了近处的稻田和远处那窝竹子的下半部分,留着竹尖上的叶子反射着夕阳熠熠生辉。
没一会就走到了那窝竹子下,这是我们去村里小学的必经之路,旁边有条十米来长的石板桥,过了桥,再走二十多分钟就能到学校。
月月踮起脚把袋子挂到了第三节牛角的位置,然后嫌弃的晃了晃手里的竹竿扔到旁边,欠身在河边洗准备洗手。
我闻到一个很奇怪的臭味,心想是刚才挂上去的坏鸡蛋散发出来的,就往后退了几步离了远点,把手里的香撮起点燃,低下身把地面上的竹叶拨开一小片地,插了上去。
却看到不远处的另外一窝竹根下边儿已经插了有几炷香了,想来应该是其他人也来挂过夭折的蛋仔。
突然,月月像是被什么东西吓到了,“啊呀!”的叫了一声。
我把嘴里叼着的狗尾草拿下来扔掉,起身忙问“怎么了”,她妞着自己的左胳膊在看,但是好像在盲区里什么看不到,一边说:“好像被竹刺到了。”
我凑过去说:“我看看。”
她把胳膊凑到我眼前,白净的胳膊上有两个间距一指宽、大小不一的小孔,在往外面渗着血。我说着“忍忍噢”同时伸手挤了一下伤口,流出了更多的血,然后渐渐的流出的血变成了暗红色。
“嗯,血变成黑色了,是不是刺上有毒噢。”我沾了一点在手指上,在她眼前晃了晃,然后回头想看她是被什么刺扎到的,但没看到。
“没事。”我想着电视剧里的桥段,把嘴唇凑上去,说:“我给你吸出来。”
说完就把嘴巴凑上去用力的吸了一口,吐出来一大口深红色的血,然后又吸了一口,直到已经吸不出来,吐出了红色。便心想没事了,一边在旁边捧水起来漱了下口说:“哈现在应该没事了,我们回去让闽叔看一下。”
她似乎也没有觉得很痛,摸了摸伤口“嗯”了一声便转身带我回去了。我回头看一眼,身后的竹林淹没在了远山的阴影里失了颜色,被河边晚风晃得张牙舞爪,回头的隐约间,我似乎看到竹子上盘踞着什么东西摇摇晃晃,但仔细一看又没了踪影。
回到月月家,闽爷爷正坐在院子边的灯下编竹篓,白炽灯挂着有些摇晃,电压不太够,发着微黄的光。
我们说了一下月月手臂上的伤口,他伸手稳住了灯仔细看了伤口,说应该没有大碍。
我想着电视剧里的桥段也觉得应该没事,就道别回家去了。
回家做了个漫长的噩梦,梦里天旋地砖,鬼怪回闪,却什么内容都没有,一直到早上起来觉得脑袋迷迷糊糊,全身都在痛。
停云
第二天本来正常的去上学,和月月碰到面之后走出她家门时,却被河边的上的人群吸引了,她不嫌事大,带着我跑过去看怎么回事。
路上就听年纪相仿的几个小孩儿说桥边上吊死了个人。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死去的人。
他静静的挂在昨晚我们挂毛蛋的那窝竹子的其中一根上,竹竿被压弯,垂到了河中心,一根绳子系在竹尖上,另一头挂着他的脖子。他光着脚悬在空中几乎触到水面,穿着棕色短裤,青布短袖衬衣,领口的衣服被血染成了暗红色,脸色苍白,微张着嘴,双手下垂。
下面河水平静,却涟漪不止,抬头仔细一看才发现那人指尖依然在往河里滴着血。
四周只有竹子之间摩擦着吱呀在响,那血滴在水里一点声音都没有,两岸虫鸟皆静,停云止水,竹叶与血滴一起悄无声息的砸在水面上。
周边站着的村民们从旁边划了一只小木筏过来,在想办法把他从竹子上取下来。
那条取下来的东西,并不像是普通的绳子,更像是几条...青竹篾?
大人们在旁边不让我们看,催着我们赶紧去学校,我也感觉有些发毛,便拉着月月跑开了。
竹篾是一种从竹子表面用篾刀分层分出来的薄竹片,是编织竹制品的中间材料,可以用来编比如竹凉席、做筛网之类的器具,能有几米长,宽约一指,厚度不到半毫米。对折易断,但拉力很好,可以用来捆东西。青竹篾是竹竿分层的最外层,边缘十分锋利,一不小心就容易割到手。
我边往桥边走边想,觉得明白了他明明是上吊而亡,却流了这么多血,兴许是竹篾割破了脖子。
往后很多年,那个画面都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那种十分怪异的场面,他用竹篾把自己吊在河中心,那种感觉就像,河里的一条鱼,被鱼竿拉了起来,然后定格在了半空。
放学一路上月月都在絮叨说自己的胳膊上的伤口有点疼不太舒服,回去应该拿点药酒来擦一下,我看了一眼那两个孔已经在发黑了,便表示深刻认同。
闲聊间又走到了那个桥下,我们看到所有的东西都被撤走了,连昨晚我们挂上去的麻布袋也被收走了,那片竹林看着比我们印象中还干净点。
“唉早上那个人太惨了,上周他还来我家借锯子呢。”月月走在前面还在感叹这个事情,手里拿着根捡来的棍子有一下没一下的打着。
“嗯嗯...”我有一句没一句的和她搭着话,跟在她身后顺着小路走上了桥,下意识的往早上挂着人的位置看过去,意外发现竹头上有什么东西在反射着夕阳闪闪发光。
月月还在一边说一边往前走,我的目光顺着那个反光的东西往下看,停在了桥中间。
“月月!”我连忙叫住了她。
她停在桥面上,回头看我一眼,然后又狐疑的左右看了看,问:“怎么了?”
我缓步走过去,看到离她不到一米远的地方锤下来两根半透明的蜘蛛丝,相比蜘蛛丝,它看起来更像是两根鱼线,但看起来很轻,在空气中飘着,成一个歪歪扭扭的U字,高度刚到我们的鼻子,另一头就接在反光的竹头上。
“嗯?”她也注意到了自己眼前的这根线,往后退了两步,用手里的棍子打了一下,棍子刚碰到,那根原本软绵绵飘着的线“嗽”的一声就绷紧收了上去,电光火石之间就消失了,把我们俩吓了一个激灵,连忙退回了桥头的土路。与此同时忽然起了一阵风,旁边的竹子开始发出摩擦的声音,那声音时上时下,仿佛是有个什么东西在竹竿上跳来跳去。
我俩赶紧往回跑,恍惚间回头看了一眼,只见竹林上的阴影之中,倒挂着一个巨大的黑色蜘蛛,得有一米多高,黑得纯粹而彻底,一团漆黑,还在往四周散发着一些黑色的烟雾,除了一团黑和几只腿以外,没有任何细节。它静静的倒挂在那里看着我们,和我们对视。
钓线鬼
“果然来了。”几个大人听了我们说的话之后在附近看了一圈,但是毫无发现,只听到旁边的一个老爷爷感叹了一句。
“果然?”我想循着话头问下去。
他卷了卷自己手里的烟叶,却只道:“小孩子不要什么都打听。”
“是钓线鬼。”旁边的男生一本正经的接话说道,他看起来比我们大两三岁,穿着一身白色背心,身上被晒得黑黑的。
嗯,似乎有所耳闻,但我们并没有真的见过,那是一种极具当地特色的精怪,我们这片地区竹林茂密,钓线鬼便生活在那些白天也不见天日的竹林之中。是一种拳头大小的黑色毛团,长着六只脚,远远的看起来像是一只大个头的蜘蛛。害怕阳光,平时以捕食鸟兽为生,会游泳,能潜水,习惯于趁夜色沿着河岸迁徙。以前叫它们河瓢,十分胆小,却又很奸诈,善于暗算和偷袭,三五只合起来能猎杀一只野狗。
本镇有记载,说是前饥荒年月,干尸遍地,无人安葬,钓线鬼附着尸体便能快速成长,直径能到半米有余能偷偷杀人,并伪装成自杀。个头虽大,其实绒毛占了大部分,本体像是一只长了六条长腿的小老鼠。
“可是这里没有死人呀。”我毫不避讳的说了一句。
“你们没听说吗?”他露出高年级男生看低年级小孩惯有的不屑表情,我们以为他要说今天早上这里有个人吊死了的事情,却没想到他像是透露秘密的小声说:“今天早上这个竹林里找到了一具胎儿尸骨。”
我俩瞪大眼睛看着他:“哈?”
他好像阴谋得逞的样子,接着说:“昨晚不是有个人在这里吊死了吗,警察过来搜查,就发现河边的那个竹窝里藏着个布袋子,里面包着个胎儿,都放了好几天了。”说着他一边指向昨晚我们挂蛋壳的那窝牛竹的旁边一窝,那里已经被扫干净了,还被清出了一片路,仿佛那里往来的走过好多人。
我听完感觉头皮炸了一下,傍晚的风顺着后颈抽走了身上的热气,回头和月月交换了一下眼神,想起昨晚我们来挂蛋壳的场面一阵后怕,她也是被吓得够呛,往后退了两步看着那片竹子:“啊?真的吗!”
“嗯,”他煞有介事的说:“虽然叔叔们没有头绪,但我觉得昨晚那个人就是被钓线鬼杀掉的。它们就是喜欢这样捕猎,在人的必经之路上用网做一个陷阱,等人碰到的时候用竹子的弹性把人吊起来。”
“可是昨晚的那个人不是被竹篾吊起来的吗?那显然是人为的吧。”我一边思考一边说道。
那个男生想了想,好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却又听到刚才说话的那个老人说:”它们很聪明,会用一种蛛网一样的东西把人吊起,那个网在人死之后就会变成一些常见的东西,绳子、布条之类的。“
“啊你们快别说了,听着起来怪科学的,还挺吓人...”月月赶紧让他打住,话还没说完,被旁边的大人们吸引了注意力。
听到他们在商量说这个东西有危险,带着人把周边的竹子砍了,清出一片地来,浇了一圈汽油,天黑前就把这两窝竹子一起烧了。
我坐在月月的院子里远远看着那片竹子噼里啪啦烧起来,旁边还有些人在围着四个方向放鞭炮,透过鞭炮的青烟我隐约看到火焰中有什么东西在挣扎,一些尖锐的叫声从鞭炮声中渺渺飘来。
“说来,”闽家爷爷在旁边看着我们,说:“听说河瓢是看不见的,你们小娃娃的眼睛果然要不一样点,哈哈哈哈,还好你们命大。“
月月看着远处火势渐凶,然后摸了一下自己手臂的伤口,歪头对我说:“唉?不疼了唉。”
我凑过去一看发现黑色已经散去,又给她按了两下,好像确实没事了。
酒价
案子本身,虽说是半条人命,在那个年代却也并不稀奇。
警察们过来听说几个村民把竹林烧了这个事情,觉得大家有些唐突和愚昧,但没有引起什么不好的后果,也只是批评了两句。
事后听传闻说那晚河边上吊的那个人算是自杀,证据链充分。另外,也找到了那个弃婴的母亲,是隔壁村子的一个姑娘,怀孕之后很害怕,也没有和谁商量,自己操作了之后趁着夜色扔到了这边。回去也没过几天,也是很巧合的用布绫上吊去世了,出于名声,大家并没有流传这个事情,我也只是在酒桌前听舅舅那个在派出所工作的朋友提了一段。
我把酒壶提出来打算替他把酒满上,顺口问起上吊那条布绫的细节,他却只是说:“女娃家家别管这些晦气的事情。”
我便把酒壶拿进了楼梯间里不给他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