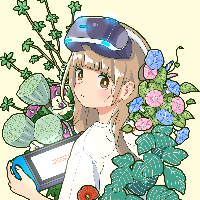蜃景
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节临端午才等来了个好天气,天刚开始黑的时候,我把下午采到的一背篓草叶扔在水缸边上,准备拿出来洗一下再拿进厨房煮洗澡用的水,却看到外公慌慌张张的从院子外小跑进来,月月也紧跟在后面。
只见他大步走进柴房里,扛着一个抽水泵出来,看了一眼月月又看了一眼我,说:“你们两个去把水管抱出来。”
我也紧了一下眉头,放下手里的水盆跑了过去,一边问月月说:“怎么了啊?”
“啊啊,是张大嫂那边,他们家的房子烧起来了。”月月说的话不太利索,但卷水管的动作很快,然后滚了一个在我面前,自己又去卷另一个,我抱起水管便跑了出去。
张大嫂是我家的邻居,说是邻居,在那时候的农村里房子也隔着近百米,那是个有五间屋的草房子,三面都长着大片的竹子,正面是一块朝西南方的坝子,坝子外边有一块宽度不到十米,长度百米有余的水田。
那些年头正处于建筑材料换新的节点上,住这种草房的家庭不在少数,所以这并不是家境贫寒的象征,只表示还没开始新修房子。正好相反,他们家的生活向来都还算富足,丈夫去了沿海务工,她和自己的儿子住在一起。
我抱着水管走出转角才看到那个房子,情况比较糟,火舌点燃了半个房顶,南边的竹子也被引燃,正朝着山上烧过去。
水田的旁边还站着三个附近的大人,其中一个顺手接过我手里的水管,然后开始往抽水泵上接,一边对抱着水管往这边跑的月月说“快点快点”,外公转身跑回去说拿电线,旁边的两个大人也顾不得挽裤子,跳进田里开始刨坑来放水泵,我也手忙脚乱的把手里的水管打散开来,大家乱而有序的在操作着。
我低着头,眼角里的水田倒映着屋子的火势,水面亮堂堂的照在所有人的动作上,月月在很卖力的在拧水管扣,头顶竹子被烧得啪啪作响,火焰推升着气流发出呼呼的声音。
然后,忽然的,从身后吹来了一阵风...
整个世界一瞬间暗了下来,声音戛然而止,火光突然消失,四周陷入寂静。
三秒钟之后,几个人陆陆续续停下了手里的动作,缓缓抬头看向房子的位置。
没有火,那个房子在夕阳下好端端的立在田对面,屋子里有个房间还亮着灯光,屋背后黑压压的竹林在轻轻摇晃。
我们几个人愣在原地,我看了一眼房子,然后眼睛在几个大人的脸上来回走了一圈,想等他们说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
“啊!啊!火不见了!”月月才指着房子后知后觉的发出一声惊叫,然后慌张的看着我,我晃了晃头看向房子,表示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对劲,有鬼啊。”其中有个叔叔方才感叹了一句,困惑的从田里抽腿站到岸上。此时我才感觉到背心有些发凉,刚才的薄薄的一层汗粘住了背脊上的衣服,又被晚风吹开了,手上黏住的湿泥巴现在有些冰凉,像是在抽空我手心里的热量。
几个人都原地坐在了田坎上,其中一人说:“刚才是有火吧?你们都看到了卅?”
“如果没事,”外公深深的吸了一口嘴里的烟,站了起来,接着说:“我们叫两声他们。”,说着他提高嗓子叫道:“张大嫂!张大嫂!”
我们几个人维持着彼此的姿势,定定的看着草房的大门,那是一扇很薄的木门,上面还贴着一个褪色的福字。
过了好一会儿,一个男人从房里推门走了出来,左右张望了一下,才看到了远处田对面我的外公,大声说:“是三爷啊。”,然后好像又看到了旁边坐着的我们,“咦”了一声,说:“你们在哪坐着干啥呢?”
开门出来的是张大嫂的丈夫,几个人看到也觉得有些意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从外地回来的。
但大家都没说话,外公看了一眼我和月月,说:“你们两个把东西搬回去。”然后把目光在其他人脸上扫了一下,一歪头示意大家去房子里。
“唉?”我不太情愿,但是也不太敢跟着过去,也没多嘴便和月月抱着还没解完的水管卷上往回走。
张大嫂的丈夫好像也明白大家要过去,看到他回屋拿了两条长凳子出来,然后转身从外面把门锁上了。
田园猫
“我听说有些地方有一种磁场,可以把以前发生过的事情记录下来,然后在相同条件的时候播放。”经过好一路的思索,月月煞有其事的和我说。
我把水管扔在坝子里,然后走到水池边上,一边打开水龙头洗手,一边说:“嗯,我果然应该多跟你看点《走近科学》,我也不知道自己会遇到这种事情。“
月月也蹲下来接水洗手,一边说:“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唉?你不怕吗?”我把甩两下手,然后在腰间的衣服上擦了擦问她。
“可是我很好奇啊。”她一边洗手上残留的泥巴一边说道。
看我站着没说话,她起身把水龙头关了,然后把还在滴水的手伸过来拉着我刚擦干的手便跑了出去。
他们几个人大人正在坝子里坐着很平常的聊天,外公好像和张大嫂的丈夫说了一下怎么回事,我们跟着辈分喊了一声“刘叔叔”,然后安安静静的走在正门旁边的台阶上,背对着那个褪色的福字坐了下来。
“还是有些怪啊...”刘叔叔神情凝重的思索着,此时太阳完全沉到了山下,天边的火烧云也暗了下来,四周只剩下一些开始降温的冷光照射着他的表情。
之后他们还在说什么,但我被分了心,身后的听到撕啦撕啦,像是爪子慢慢在挠门的声音,才想起张大嫂养的那只田园猫,平时很是暴躁,经常炸毛,上个月还在我家的鸭圈里想偷小鸭子吃。心想着它可能想从门后面出来,一回头正看到它从门后的窗台上跳了出来,然后自顾的跑远了。
“不过还是谢谢大家伙,”刘叔叔的声音把我从自己对那只猫的偏见里拉了出来。他接着说:“他们母女俩自己在家,要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全靠父老乡亲们帮忙。”
几个人便客套着说没事,邻里之间不必客气,起身准备回去了。
我拉了一下旁边的月月,示意她回去了,但她好像对于大人们没有讨论出个所以然来有点不满,自顾自的在思考着什么。
也就真的无事发生,外公回家之后把之前抽水的东西放在了柴房里便开了灯回屋子里等我做饭了。
“救火啊!救火啊!”过了不到半个小时,我菜都还没切好,便听到屋后有几个人在喊着,我停下来了手里的菜刀,外公更是弹似的从藤椅上做起来,鞋子都没穿便跑了出去。我跟在后面,路过柴房的时候外公抱起抽水泵,一边跑一边叫我把水管抱上。
旁边张大嫂的房子又烧了起来,火势更加汹涌,已经看不清房子原本的轮廓,还点燃了附近的小山坡,通天的火光照亮了一整块水田,里面的竹子噼里啪啦的在炸着,热浪一阵阵的扑过来。
我把水管递给了某个人然后呆站在原地没有去帮忙,大火的热浪和着五月的夜风一阵阵的往我脸上吹,我的眼里尽是火光,背脊却在生凉。
酒事
事情大约过了两三天,舅舅抓到了两只兔子,带着朋友来外公家喝酒,还没开始吃饭他们便在桌子上聊了起来,我坐在旁边给圈里的鸭子们切草食。
“那天晚上真是妖怪...”听到舅舅的朋友在感叹,我假装无事的继续切着,耳朵却竖了起来。
舅舅给大家分了一杯酒,然后吃了一颗花生,接话道:“是啊,是怎么个事情,你们所里有内部消息吗?”
“那是当然,“那人浅浅的泯了一口酒,接着说:”那天晚上起火之前刘大就跑到镇派出所来自首了,他说他好像杀了妻子。“
说着他深呼吸了一下:”当时我值班呐,哪里见过这种事情,收拾了一下就和人回来看怎么回事,结果我们人还没到咧,他家房子就烧了。里面太惨了,宋家那个人,光溜溜趴在床上,被烧焦了,背上和头上都被斧头砍了个大窟窿,他的妻子心口被砍了一斧头,没有断气,从床边爬到了门口,后来是被火烧死的。“
我突然感觉心里像张大嫂家里养的那只田园猫对着我发火时一样炸开了毛,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宋家那个和姓张的关系不干净,当时他们俩正在屋里亲热呢,刘大之前就在外面听说了这个事情,偷偷回来几天了,躲在竹林里没回家,就等...“
我心里有些恍惚,没听明白是怎么回事,把刀放到了菜碎里,紧着眉头歪着头尝试理解他们说的话。
“然后抓到姓宋的进了他家屋子,刘大就拿着门口劈柴的斧头走进去给了他两斧头。他正在砍妻子的时候,听到你们在外面喊她,刘大才装作无事的走出来。他本来想杀了之后,放火烧房子,然后自己再偷偷回外省打工,假装自己没回来过。”
那人说到兴头上,放了一颗花生到嘴里,细细的品味着,仿佛是在给听的人一点时间理清楚事情。过了会儿才感叹了一句“知人知面不知心呐”,然后看着外公说道:“结果老爷子你带着人去找他了,他没办法,就出来应付了你们了,殊不知他那时候刚刚杀了两个人。”
“哟!”换来两人的一阵唏嘘。
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坐了过去,但酒桌上他们好像没注意到我。
“所以他把房子烧了就直接来自首了啊?”外公问道。
“他说没有烧,”那个人接着说:“他本来打算烧房子逃跑,连汽油都倒好了,但是被看到了嘛,就没有烧,自己在家里考虑了半个钟头,就直接来自首了。“
“那房子是谁烧的呢?”舅舅问出了我也很在意的问题。
“不知道呢,没查出来。我估计啊,他说谎了,估计就是他放的火...”然后他故作思索的停了一会儿,又说:“倒也是有可能厨房没人,所以烧起来的,毕竟汽油浇上了之后很容易引燃。”
舅舅轻轻的做了个拍桌子的动作,激动的说:“是吧是吧,很怪,我们那天晚上在起火之前就看到了那场火,所以才去他家的...”
之后便说起了那晚火光突然消失的事情。
吃了炒的兔肉之后便早早的去睡了,晚上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
梦里我的视角穿透那个褪色的福字,走进了房间里。桌角上靠着一把黑红色的斧头,卧室墙上洒了两道凌厉血迹,血迹下的床被已经被染成了红色,上面躺一个男人,有道血痕从卧室的床边一直拖到了客厅门面前,张大嫂侧躺地上,胸口上红白相间的伤口往外冒着血,她一只手捂着伤口,另一只手臂搭着门槛,伸手的指甲扣进了门角的木头里。
她没有动,任由额头上的血浸透眉毛,流进了左边眼睛里,将眼白染成了红色,无神的望着薄门之外我的背影。
房间里的画面似乎凝固了,空气漂浮着一些灰尘,血的味道和水煮豆腐的味道混在一起,一只猫从她身上跳了过去,跳上门后的窗台,从我的背影前跑远了。
完。